从出土文献看春秋吴师入郢之役
——对石泉先生楚郢都新说的印证
晏昌贵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
业师石泉先生在其名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的“自序”中说:
1944年春,我在徐中舒先生指导下开始写作本科毕业论文。……当进行到考订春秋晚期吴、唐、蔡师入郢这次大战役的有关地名位置时,我对于流行的解释发生了很大的疑问,感到那种说法在情理上和史料上都是矛盾百出,很难讲得通。这促使我对《左传》所记这次大战过程中涉及的二十几个地名的位置,进行了一番返本探源的重新考订,跳出隋唐以来直至近世逐步形成的旧传统框框,主要依靠更早的先秦、两汉、六朝(直到齐梁时)的古注和经过认真鉴定的有关史料,以此与《左传》所记互相印证,结果得出了与流行说法全然不同的、意外而又不得不然的新解。原来:吴师是乘舟溯淮西上,登陆于蔡境。以蔡国为第一个中继站,于此会蔡师西进,踰楚方城隘口(即“城口”三隘——大隧、直辕、冥阨,它们不在今武胜关一带,先秦时有关冥阨的一系列记载可证),入南阳盆地,到唐国(当在今河南唐河县南,而非在今湖北随州市西北之唐县镇)。又以唐国为第二个中继站,会唐师,三国联兵转南进,“自豫章与楚夹汉”(见《左传》定公四年)。这里的豫章,当是《水经注·淯水篇》所记,位于今鄂豫边界、唐河与白河汇合前、两河之间的“豫章大陂”,正在唐国西南不远处;而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今安徽寿县附近或湖北安陆南。其吴楚两军“夹汉”对峙之处,当在今襄樊市一带的汉水两岸,而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今武汉市及附近之汉水入江处。随后,吴楚之战的主要战场,实皆在今襄樊市东北的汉水左岸:大别山当在汉水东流转南的丘陵地,而非今武汉市汉阳区之龟山(亦称大别山);吴楚决战之著名战地柏举则当在今随枣走廊西口外、滚河自枣阳县境西流入唐白河后的下游北岸,与楚之麇邑(也是柏举战场的组成部分)相邻,绝不可能远在今鄂东麻城县境;清发则应是位于今襄樊市北邻,东南流,在樊城以东入汉水的清水;雍澨即《禹贡》“三澨”之一,当依清人胡渭《禹贡锥指》所考,在今樊城或其附近之汉水北岸。弄清这些地名的地理位置之后,就可以看出吴师入郢的军行路线乃由南阳盆地南下,在襄樊一带渡过汉水,长驱南进,攻入楚郢都;而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吴师进至今鄂中安陆、武汉一带之后,又东退鄂东,与楚决战于麻城县境的柏山、举水之间,大胜之后,复长驱西进,经安陆、钟祥二县南境渡汉,西南进,直下楚都(被认为在今江陵“纪南城”遗址)。另一方面,楚昭王君臣于郢都陷落前,仓皇出奔,“涉雎(沮)济江”(见《左传》定公四年),所经之地,如“涉于成臼”(汉水中游的渡口,见《左传》定公五年,杜预有注),以及楚郧公邑,都在今钟祥县境的汉水以东,即汉晋时的古竟陵县地。这在《左传》(定公五年)、《汉书·地理志》(江夏郡竟陵县下原注)都有明文记述。由此奔随,只需越过不太险峻的大洪山脉即可到达,途程并不很远。而“奔郧”之前所经之“云中”遇盗之处,又必然去郧公邑不远,故被“盗”击伤之楚王随从(名由于)可以“徐甦而从”,另一名随从(钟健)可以“负季芈[王妹]以从”(皆见《左传》定公四年)。云中又是楚王自郢出奔,“涉雎(沮)济江”之后,即进入的地方,则所济之“江”,应即成臼附近之汉江,而绝非今之长江。这样,楚王出郢后所涉之雎(沮)水亦当近汉,从而只能是今宜城平原上的蛮河下游,而绝非如流行说法所云,为今江陵附近之沮漳河。因此,作为吴师入郢与昭王奔随接合点——楚郢都就只能在今湖北省宜城县南境、汉水以西、蛮河(古雎水)下游的宜城平原上,而不可能远在长江边今江陵县北的“纪南城遗址”。根据以上的论点与论据,我写成了一篇毕业论文,题为:《春秋吴师入郢地名新释》。……对我来说,却是着手研究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开端。[1]
由此开端,石师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古代荆楚地理的艰辛探索,所得基本结论为: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不在今江陵纪南城遗址,而在汉水边今宜城南,与之相关的山川城邑,亦应位于汉水中游地带,而不在长江沿岸和江汉平原的水乡洼地。
回想当年初入石门,先生即命我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楚郢都及其中心城邑作一番新探索,以印证先生的新说。无奈我资质鲁钝,对先生的学说体系钻研不透、体会不深,只能知难而退、避重就轻,于是另撰他篇、以求速成。先生初不以为意,还对我的博士论文谬赞有加,真是令我惭愧汗颜、无地自容。
多年以来,我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虽然涉猎颇杂,然对先生之学说,念兹在兹,没时或忘。尤其是近年来研习新见之金文简牍材料,发现出土文献颇能证成先生新说,足见先生高瞻远瞩,洞见于先。今兹适逢先生百年诞辰,因在时贤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拾缀成此小文,作为对先生的纪念。文题中的“出土文献”,专指有文字记录的金文简牍史料,暂不涉及考古学遗址。传世文献所载吴师入郢之役涉及地名及路线已经石师考证者,本文亦不再讨论。石师《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的主体内容分为三节,即:“吴师入郢的军行路线”,“楚昭王君臣自郢奔随的路线”和“秦楚联军反攻与吴师东撤的军事地理形势”。本文亦分三节,分别为“吴师入郢”、“昭王奔随”和“昭王复邦”。以下分述之。
一、吴师入郢
按照石师新解,吴师入郢的军行路线是溯淮西上,会合蔡国后一路西进;通过楚方城缺口,南下会合唐师,再一路南下,直捣楚郢都。整个行军路线是先向西再转向南。
2009年,为配合工程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在随州东城区文峰塔发掘了三座墓葬,其中一号墓(M1)出土《曾侯与钟》铭文云:“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2]铜器铭文的最初整理、释写者凡国栋率先指出,铭文中的“西征南伐”是指吴师入郢之役。[3]其后高崇文结合考古发现的古代文化遗址,对吴师入郢之役的行军路线重加探讨,认为《曾侯与钟》铭文“印证了石泉先生考订的(吴师入郢的军行)路线是正确的”。[4]
但也有学者认为,铭文中的“西征、南伐”指的是西征楚、南伐越,[5]从而否定钟铭与吴师入郢之役的关联性。今按:古文献中确实有吴人西征楚南伐越的记载,比如《说苑·正谏》:“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越。”[6]《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吴以子胥、白喜、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于越。”[7]但较早的记载亦有作“东伐越”的,如《墨子·鲁问》:“昔者吴王东伐越,栖诸会稽;西伐楚,葆昭王于随;北伐齐,取国子以归于吴。”[8]伐越在伐楚、伐齐之先,《墨子》为文更合乎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当更为可信。更重要的是,钟铭“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语意一贯,“西征南伐”均指“加于楚”,“乃”字尤为明证,不应在中间插入南伐越国事。这是勿庸置疑的。
石先生对吴师入郢军行路线的新阐释与传统说法重要区别的关键点,在于对吴蔡联军是否通过楚方城的不同认识上。传统看法以为吴蔡联军“舍舟于淮汭”后,又经豫南鄂东之“义阳三关”南下,复西进,与楚军夹汉水对峙。石师则认为大隧、直辕、冥阨并非后世之“义阳三关”,应即《左传》所记之“城口”,亦即楚方城缺口,吴蔡联军实由方城缺口南下攻入楚腹心地区。新出清华简《系年》有力地支持了石泉先生的新解。《系年》第18章云:
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许人乱,许公佗出奔晋,晋人罗城汝阳,居许公佗于容城。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门方城。遂盟诸侯于召陵,伐中山。晋师大疫且饥,食人。楚昭王侵伊洛以复方城之师。[9]
有关晋吴联军攻楚亦见《系年》第20章:“晋简公立五年,与吴王阖庐伐楚。”可证晋吴联军攻楚确乎信而有征。在《系年》简正式刊布的同时或稍前,整理者李守奎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概括《系年》有关吴师入郢之役的记载,指出这场战争是晋与吴联合伐楚,晋、吴联军是从方城外攻入,认为“石泉先生曾经对吴师入郢的进军路线作过精辟的分析,认为吴人自方城攻入,简文证明(石泉先生)完全正确”。[10]后来在正式发表的会议论文中,重申前论,认为“吴人入郢和昭王出奔的路线,石泉先生有过非常深入的研究,《系年》可以证明他的许多结论是可信的”。[11]随着简文的正式刊布和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注意到《系年》与《春秋》经传的重大差异,从而否认《系年》18章中“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门方城”与吴人入郢之役的关联性。[12]为此,我们需要重新疏理《系年》与《春秋》经传之异同,以求得历史事实之本相。
《春秋》定公四年纪事多达16条,为便于比较、分析,今备列如下(文前序号为笔者所加):
(1)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陈侯吴卒。
(2)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
(3)夏四月庚辰,蔡公孙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
(4)五月,公及诸侯盟于皋鼬。
(5)杞伯成卒于会。
(6)六月,葬陈惠公。
(7)许迁于容城。
(8)秋七月,公至自会。
(9)刘卷卒。
(10)葬杞悼公。
(11)楚人围蔡。
(12)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
(13)葬刘文公。
(14)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
(15)楚囊瓦出奔郑。
(16)庚辰,吴入郢。
《左传》定公四年之叙事次序略如下举(为便于比较,我们将《春秋》经文的序号标注于前):
(1)无传。
(2)四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乃辞蔡侯。
(4)及皋鼬,将长蔡于卫,卫侯使祝佗(按:即子鱼)私于苌弘曰:“闻诸道路,不知信否。若闻蔡将先卫,信乎。”苌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卫,不亦可乎。”子鱼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苌弘说,告刘子,与范献子谋之,乃长卫侯于盟。
(5)-(7)无传。
(8)反自召陵,郑子大叔未至而卒。
(9)、(10)无传。
(3)沈人不会于召陵,晋人使蔡伐之。
(11)夏,蔡灭沈。秋,楚为沈故,围蔡。伍员为吴行人以谋楚。楚之杀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孙嚭为吴大宰以谋楚。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蔡侯因之,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
(12)、(13)无传。
(14)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
(15)子常奔郑。
(16)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
观上文,《左传》实际上只详细叙述了一件事,即吴师入郢之役。又分两个阶段:一是召陵会盟,重点在会盟之礼仪;二是蔡吴唐联军伐楚入郢,重点在过程。为了保持叙事的连贯性,《左传》不惜改变《春秋》经文叙事的时间顺序,将经文第3条蔡灭沈移置于第4条后第11条前,中间省略了经文的第5-10条,这样,蔡灭沈、楚围蔡、蔡吴联军伐楚,前后连贯,而见于《春秋》和《系年》的迁许容城和晋伐中山就成了无传之文,有关历史事实被消解于无形。兹将《春秋》经传与《系年》记事的先后次序及其异同列表如下:
表1:《春秋》经传与《系年》记事之异同
观上表,《春秋》说会诸侯于召陵是“侵楚”,《左传》则说“谋伐楚”,杜预注:“于召陵先行会礼,入楚竟(境),故书侵。” 孔颖达《正义》:“诸侯既入楚境,先行会礼,后乃侵之。”[13]《左氏会笺》则说:“不果伐而还,故曰侵。此春秋第一大会。而称侵,伯(霸)业之衰而可见焉。合诸侯止于此。”[14]从《左传》的叙述看,确是先行会礼,重在会盟上的位次之争,而无晋侵伐楚国事。而《公羊传》何休《解诂》则称“诸侯杂然侵之”,并不否认侵楚之事。[15]
“许迁于容城”不见于《左传》,《系年》则称“居许公佗于容城”。2003年,河南省南阳市八一路中原机械工业学校工地6号墓(M6)出土一件春秋晚期青铜敦,有铭文2行6字,[16]黄锦前释为“许子佗之盏盂”,认为此即《系年》之“许公佗”,亦即《春秋》定公六年之“许男斯”。他还说:《系年》“所记有关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历史背景亦皆与许子佗盏盂的出土情况相吻合,亦有传世文献可相印证,其具体过程也与文献记载可对应,凡此种种,应决非皆系偶然巧合,而只能说明《系年》的有关记载是准确可靠的。”[17]《系年》“晋人罗城汝阳”之汝阳,亦见北京大学藏秦简《水陆里程简册》,写作“女阳”,所记行程里距为:“鲁阳到汝阳百一十里,汝阳到轮氏八十九里,轮氏到雒阳百一十里。”[18]鲁阳在今河南鲁山县城关,雒阳即今洛阳市北。根据简册所记汝阳距离鲁阳和雒阳之间的里程及相关地理形势推测,汝阳应位于今汝州市纸坊乡境内的汝水北岸。[19]容城,传统看法定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从秦水陆里程简册看,容城与汝阳之间的距离超过110里(秦里,约合今46千米),简文称“晋人罗城汝阳,居许公佗于容城”,则容城与汝阳应相距不远,容城或许更靠北而近汝阳。许迁容城之前位于楚方城之内的析地(又名白羽,今河南西峡县),晋乘许国内乱之际将其从楚方城内迁往方城外安置,显然是出于图谋楚的统一安排。因此,本条有关许迁容城的记事就与下条晋吴联合伐楚密切相关,二者不可分割。
《系年》晋、吴联军“伐楚门方城”不见于《春秋》经传,亦不见于其他传世文献记载。“门”字原作
,整理者认为是动词“门”专用字,“训为攻破”。[20]陈伟认为是“攻打方城之门,并不一定有‘攻破’的意思”。[21]黄锡全则以为“門是鬥的讹变,读若‘环’,意为环绕方城,有环攻、围攻之意”。[22]整理者还引述《左传》文公三年“门于方城”的记载,按是年楚师围江,晋救江,率师伐楚,“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很难说已经攻破楚方城,陈伟的意见最为可取。《左传》多有“门于某门”之记述,如成公八年:“郑伯将会晋师,门于许东门,大获焉。”襄公九年:“诸侯伐郑,……门于鄟门。”前一个“门”为动词,意为攻打;后一个“门”为名词,指城门。名词的门也可省略,如庄公十八年:“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杜预注:“攻楚城门。”有时也承前省略动词后面的宾语,如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杜注:“攻曹城门。”简文中的“门方城”,应指攻打楚方城隘口,亦见城口(见上举石师“自序”所述)。虽名为“城口”,实等同于城门,故简文有“门方城”之说。
《春秋》经“晋伐鲜虞”应即《系年》晋伐中山。从《系年》看,此次晋伐中山,“大疫且饥,食人”,可谓损失惨重,[23]《左传》不书,大约是“讳之也”。至于《系年》“楚昭王侵伊洛以复方城之师”,则应指楚昭王二十五年(前491年、鲁哀公四年)“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事,[24]已在吴师入郢之役十五年之后,属昭王复邦之举措,与吴师入郢之役无直接关联。
通过以上疏理,可以发现,《系年》与《春秋》经传的区别,一是晋吴伐楚之有无,二是叙事先后次序之差异,二者密切相关。上文述及,许公佗(许子佗)亦见于考古出土之青铜器铭文,人物、地点、年代均相契合,足证《系年》记事不误。[25]《春秋》系鲁国编年史,传言为孔子所编定,其中明确记录鲁定公参会、退会、回国之经过,亦确然可据。《左传》成书年代约与《系年》相近,其史料来源则颇为多元,但以晋、楚二国为主。[26]那么,如何解释它们之间的矛盾呢?李守奎认为“晋吴伐楚”即《春秋》经文会召陵“侵楚”事,于先后次序之矛盾略未涉及。[27]马楠以为鲁定公四年春有召陵之会,谋侵楚而未成;秋,楚人围蔡,晋伐鲜虞(中山);冬,吴伐楚入郢,晋伐方城以助蔡、吴之师。[28]然此说不符合《系年》叙事晋人先伐楚后伐中山之次序,恐难凭信。陈民镇据《系年》第20章“晋简公立五年,与吴王阖庐伐楚”之纪事,认为晋吴合兵伐楚在鲁定公三年,其先后次序为:晋吴合一、门楚方城——召陵之会——吴师入郢。[29]但这样一来,许迁容城亦需提前一年,与《春秋》不合。今按《系年》记事常有提前一年的例子,比如第15章楚围陈在庄王十六年、鲁宣公十一年,《系年》却记于庄王十五年。此类例证尚多。大约《系年》类似古代纪事本末体史书,重在说明事情之原委,不像编年体史籍,时间观念常有混淆,但先后次序却不容颠倒,否则因果不明,有违纪事本末之体。《系年》第20章之“晋简公立五年”,当为六年之讹误。[30]孙飞燕认为召陵之盟有二次,《春秋》经传记载的是第一次,在三月;简文所说是第二次,在秋天楚围蔡之后,先后顺序是:三月,第一次召陵之盟,谋伐楚;六月,迁许于容城;秋,楚围蔡,晋、吴攻打楚方城;第二次召陵之盟,率诸侯伐中山;冬,柏举之战,吴入郢。[31]如此,似可解决《春秋》与《系年》的矛盾,但二次召陵会盟史载不明,其详还有待探索。
细读《春秋》经文,鲁定公四年三月会诸侯于召陵,侵楚;五月会诸侯于皋鼬。杜预注:“繁昌县东南有城皋亭。”《公羊传》作“浩油”,《九经古义》引《盐铁论》作“诰鼬”。[32]其地在今河南许昌市南、偃城县北,还在召陵的西北方。[33]对于这两次会盟,《谷梁传》说:“后事而再会,公志于后会也。后,志疑也。”[34]何以“志疑”?传文未明。今联系《系年》简文,颇疑所谓“后事”者,当为晋盟诸侯于皋鼬以伐中山事;前事则谓会诸侯召陵“侵楚”事。召陵地在南,皋鼬地在北,或可为证。《左传》于“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后有一节叙及晋荀寅求货贿于蔡候弗得,然后他对范献子说:“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35]可见“中山不服”的危机最终导致晋人改变会盟伐楚的初衷,转而攻打中山。《系年》“遂盟诸侯于召陵伐中山”,召陵为始盟之地,且与皋鼬邻近,召陵可以概指皋鼬。“遂”,相当于“竟然”、“终于”,杨树达《词诠》卷六:“遂,副词,终竟也。”[36]《系年》据召陵会盟之“后事”,转述会盟之最终结果,乃有“伐中山,晋师大疫且饥,食人”之记录。据以色列学者尤锐(Yuri Pines)考察,《系年》实为楚人作品,但其史料来源则颇为多元。第18章的史料来源以晋、楚二国的史料为主,“晋迁许”、“门方城”、“伐中山”诸记事均当来源于晋国史料(或晋国官档)。[37]当楚人(《系年》的编者)根据晋、楚二国史料编写《系年》第18章时,遂略加剪裁,以召陵会盟的结果为线索,书写“遂盟诸侯于召陵伐中山”于“迁许容城”和“伐楚门方城”之后。一个“遂”字,强调了召陵会盟的结果,并非在召陵盟后另有一次召陵之会盟。
总之,由清华简《系年》可以确认,吴师入郢之役或稍前,晋吴联军曾攻打楚方城,从而在一定程度证实石师有关吴师入郢之役是乘舟溯淮西上,一路西进,然后踰楚方城隘口,南下南阳盆地,“自豫章与楚夹汉”,五战五胜,直捣楚都。新出《曾侯与钟》铭所谓“西征南伐乃加于楚”,也在宏观上印证石泉先生关于吴师入郢的军行路线。
二、昭王奔随
上文曾引《曾侯与钟》铭“西征南伐”以证吴师入郢之行军路线,实则铭文更能说明昭王奔随之史实,今不惮词费,将全铭具引如下:
惟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与曰:伯括上庸,左右文武。挞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庀淮夷,临有江夏。周室之既卑,吾用燮蹙楚。吴恃有众庶,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荆邦既变,而天命将误。有严曾侯,业业厥圣。亲博武功,楚命是静。复定楚王,曾侯之灵。穆穆曾侯,庄武畏忌,恭寅斋盟。伐武之表,怀燮四方。余申固楚成,改复曾疆。择选吉金,自作宗彝,龢钟鸣皇。用孝以享于辟皇祖。以祈眉寿,大命之常。其纯德降余,万世是尚。[38]
铭文借曾侯与之口,讲述曾国被分封于南土的原因及使命,重点强调在吴师入郢之役的过程中,曾侯“亲博武功,楚命是静,复定楚王”之功绩,因此得以“申固楚成,改复曾疆”——重申与楚国的盟约,恢复曾国的疆土。于是作此钟铭,以示纪念。钟铭当铸于吴师入郢、昭王复邦后不久。[39]可以确证吴师入郢时楚昭王奔随之史实,亦可证铭文中的曾国即传世文献中的随国。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篇战国竹书《楚邦不称》,亦涉及昭王奔随事,原释文多有误,今参据后续研究成果,将相关部分移写如下:
就昭王之亡,要(遇)王于随,时战于澨,战于梁,战于长随、曲随,三战而三捷,而邦人不称勇焉。[40]
该篇主要讲述叶公子高的两项功绩:一是楚昭王失邦出奔到随之后,叶公子高遇王于随,并率部与吴军作战,三战三捷,帮助昭王复国成功,但他没有宣传自己的战绩,邦人不知其勇,故不称举其英勇;昭王复国,叶公子高用冠遮住脸保护昭王返回郢,邦人不知其谁,故不称赞其美德。另一件是有关叶公平复白公之乱事,因与本文无关,不备录。
但文献中并无昭王奔随时有关叶公事迹的记载,简书中提到的三战之地亦不见于古书,“澨”、“梁”(或释作“津”)更象是通名,常作为地名的后缀,泛指某种地貌形态,如吴楚屡次交战之地“雍澨”(见“前言”所举石先生“自序”),以及“陆梁”(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等,至于“长随”“曲随”亦于史无征。简书更象小说家言,羌非故实。
石泉先生在考证完吴师入郢、昭王奔随的路线之后有言:“楚郢都位于吴师入郢、昭王奔随的连接点,就只能在今蛮河(古雎水)北岸,汉水以西的宜城平原上,与今宜城县南15里、郑集东侧的楚皇城遗址正合。”[41]这是合乎逻辑的推论,石先生另有专文详考楚郢都地望所在。而关于昭王时期的楚都,却另有新的发现,这就是清华大学所藏的战国竹书《楚居》。《楚居》举述历代楚君的徙居地,其中关于昭王有如下记录:
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美郢,美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阖庐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秦溪之上复徙袭美郢。[42]
据《楚居》,在位27年的楚昭王曾有5次徙居,涉及4个地点,阖庐入郢前分别居住在秦溪之上、美郢、鄂郢、为郢,阖庐入郢后又回到秦溪之上,然后徙居美郢,似乎有重复循环变换居所的意味。在阖庐入郢前,所居地是“为郢”,这个为郢,据简书,又可以简称“郢”,很显然,简书的“阖庐入郢”,指的就是这个“为郢”,而不可能是其他地点。
《楚居》中的为郢始自楚文王,历经文王、穆王、庄王、共王、康王、孺子王、昭王、献惠王,是《楚居》中历经楚王最多的一个“郢”,应该也是春秋时代作为都城时间最为长久的一个“郢”。清华简的整理者说:“春秋楚邑有蒍,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子玉复治兵于蒍。’ 蒍或与为郢为关。《通志·氏族略》:‘蒍氏食邑于蒍,故以命氏。’‘蒍氏’又作‘薳氏’。今淅川丹江口水库一带有蒍氏家族墓地。”[43]黄灵庚沿袭整理者的思路,也把“为郢”之“为”读为“蒍(薳)”,但他根据清代《春秋传说汇纂》的意见,认为蒍(薳)在今湖北京山县西百余里汉水东岸。[44]同为清华简整理者的赵平安后来撰文,从楚文王迁都的实际情况出发, 结合楚灵王时期的史实,判断为郢就是《左传》昭公十三年、《史记·楚世家》灵王十二年的鄢,在今湖北宜城西南,即考古发现的宜城郭家岗遗址。[45]近来赵庆淼结合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和新见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记载,认为“为郢”的地望应该在今宜城东南的楚皇城遗址。[46]我们认为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石先生吴师入郢、昭王奔随所涉及地点和路线的考察。
吴师入郢之后的昭王徙居地秦溪之上,始自楚灵王,历经平王和昭王,《楚居》说:“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竞平王(即楚平王)即位,犹居秦溪之上。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美郢。”吴师入郢后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美郢,此后《楚居》不再出现徙居秦溪之上的记录,可见它作为楚王居地的历史已经结束了。
关于这个“秦溪”,整理者李守奎初以为即《左传》之乾溪,并根据杜预注,定在今安徽亳州市东南七十里,与城父村相近。[47] 但他后来改变看法,根据清华简中吴王夫差写作“夫秦”,而将秦溪读作“溠溪”,溠溪亦即溠水,秦溪之上“应当就是位于秦溪两岸的一个地方”,又说“之上”可能与“(同宫)之北”类似,是指方位的北面和秦溪的上游。由于秦溪之上与随相邻,李守奎认为《楚居》中的“徙居秦溪之上”,实际上就是指昭王“归随”。[48]黄锡全不同意李说,以为秦溪若为溠水,则与随(曾)都过于邻近,于是他从章华台逆推秦溪之上,以为其地当在西汉华容县境内,其确切地点,或即《水经注》所记之“离湖”,为今监利县之乾溪或乾港湖。与楚灵王“乐乾溪”非一地。[49]赵平安以为秦溪即乾溪,但他认为此秦溪(乾溪)即《水经注》之溱水,亦即今溱头河,发源于确山与泌阳交界处,于汝南沙口入古汝水。[50]从上文复原晋吴攻方城及吴师入郢的行军路线看,阖庐入郢后方城外一带已非楚人有效控制的地区,昭王在吴人入郢后不可能迁徙到方城外的城父或今河南确山一带,[51]李守奎前说和赵平安说都是无法成立的。至于黄锡全的“华容说”,则与灵王“乐乾溪”相隔太过悬远。按楚灵王晚年的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吴国势力的崛起,主要用兵淮域。上举《曾侯与钟》铭说曾国初封,是“营宅汭土,君庀淮夷,临有江夏”。“汭土”,徐少华以为当为江汉之地或汉阳之域,与文献“汉阳诸姬”相呼应。[52]陈伟读作“裔土”,泛指边远之地。[53]李学勤以为正是今随州一带,并怀疑这里的“汭”可能读为“㵐”,是㵐水与溠水的交汇处。[54]韩宇娇进一步指出即随州淅河镇北之庙台子遗址。[55]王恩田亦以为“营宅汭土”即在随地营都建国。[56]曾(随)“营宅汭土”而能“君庀淮夷,临有江夏”,可见随国故地在当时的确具有东统淮夷、南临江夏之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楚灵王“乐乾溪”的目标为东征东吴、南临荆楚,可能与曾侯与有同样的效果。
总之,我们同意李守奎的后说,秦溪之上应即溠水之上。古代地理方位名词之“上”、“下”是指河流的上游和下游,如放马滩古地图中的“上临”、“下临”,“上杨”、“下杨”,“上辟磨”、“下辟磨”等。[57]古溠水发源于随县西北150里之栲栳山,东南流入涢水。秦溪之上或在古溠水源头附近地带。[58]
三、昭王复邦
吴人入郢、昭王奔随、昭王复邦是三个密切相关的环节。《左传》定公四年之末尾记叙了申包胥入秦求援颇富戏剧性的一幕,接着在定公五年写道:
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概王于沂。吴人获薳射于柏举。其子帅奔徒以从子西,败吴师于军祥。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吴师败楚师于雍澨,秦师又败吴师。吴师居麇。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焚之而又战,吴师败。又战于公壻之溪,吴师大败,吴子乃归。[59]
上述记载中的诸战地石师有详考,出土文献亦颇有与之互证者,今略为举述如下。清华简《系年》第15章:
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伍员为吴太宰,是教吴人反楚邦之诸侯,以败楚师于柏举,遂入郢。昭王归随,与吴人战于析。吴王子晨将起祸于吴,吴王阖庐乃归,昭王焉复邦。[60]
关于“与吴人战于析”之析,整理者以为即《左传》中的“沂”,引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定其地在今河南正阳一带。[61]袁金平、张慧颖以为“析”或即“慎”字异体,“慎”在今河南正阳一带,与整理者说同。[62]李守奎以为即《左传》迁许于析实白羽之地,在淅川沿岸,今河南西峡县稍北。[63]《战国策·楚策一》及《淮南子·修务训》均谓秦楚联军击破吴于濁水之上,石师以为“沂”即濁水,在今唐河县西南。[64]
上博四《昭王毁室》:
昭王为室于死湑之浒,室既成,将落之,王戒邦大夫以饮酒,既型,落之。王入,将落。有一君子丧服冕,廷,将跖闺。雉人止之曰:……雉人弗敢止,至闺。卜令尹陈省为视日,告:“仆之毋辱君王,不幸仆之父之骨在于此室之阶下。仆将掩亡老,以仆之不得并仆之父母之骨,私自埔。……”王曰:“吾不知其尔墓,尔姑须,既落,焉从事。”王徙处于坪澫,卒以大夫饮酒于坪澫。因命至俑毁室。[65]
简文大意是:楚昭王新建一室,行将落成,召集众大臣宴饮。这时,有一位穿戴丧服的“君子”想要进入而被守卫阻拦。当听说他的父亲葬埋于宫室的台阶之下、“君子”欲迁骨将其父母合葬时,楚昭王乃下令更改饮酒之地,并拆除了该宫室。紧接着《昭王毁室》抄在一起的另一篇《昭王与龚之脽》说:
昭王跖逃珤,龚之脽驭王。将取车,大尹遇之,被裀衣。……王曰:“……天加祸于楚邦,霸君吴王身至于郢,楚邦之良臣所暴骨,吾未有以忧其子。脽既与吾同车,或[舍之]衣,思邦人皆见之。”[66]
《昭王与龚之脽》中的“天加祸于楚邦,霸君吴王身至于郢,楚邦之良臣所暴骨”当指吴师入郢之役,具体地点很可能就是《左传》所载子西所云“父兄亲暴骨焉”之麇地,因而《昭王毁室》中的“死湑之浒”,亦可能即《左传》之“公壻之溪”,《昭王毁室》中的“君子”之父或为此战之战死者,而被埋在公壻之溪。公壻之溪,石师推断在今河南泌阳县东、长城山丘陵地西侧的某一山口内,傍溪之处。[67]
楚昭王曾从秦溪之上迁往美郢,“美”字原写作
,据《周礼》,又作“媺”,楚简文字常用作“
美”。据牛鹏涛研究,其字与麋通假,而麋字又常写作麇或麏。[68]我们认为这个意见可取。但他将《楚居》中的郢定在今湖南岳阳一带,则恐难凭信。这个麇当即吴楚战地之麇,邻近柏举,在今湖北襄阳东北、滚河入唐白河后的唐白河下流东岸。[69]竹添光鸿在研究《左传》相关记载时曾指出:“吴初败楚于雍澨,司马戌又败吴师;此年吴师又先败楚师雍澨,而秦师败吴师于雍澨。则雍澨为苦战之地,而麇为近雍澨之都城无疑。所谓父兄亲暴骨焉者也。盖雍澨之师败,而保于此矣。”[70]其说甚为有见。亦可为《楚居》
郢即《左传》麇地之一证。
《楚居》所见昭王徙居地有四,本文已考述其三:为郢、美郢、秦溪之上,另有一处鄂郢,于此附带述及。学者或以为鄂郢即汉代西鄂县,在今河南南阳北;[71]或以为东鄂,今湖北武昌。[72]今按:今湖北随州一带亦为古鄂地。1975年,湖北随州羊子山曾出土带有“鄂侯”铭文的青铜器,[73]上海博物馆、洛阳市均征集到鄂候器,2008年澳门文物市场亦有鄂候青铜鼎出现,时代均在西周初年。[74]对于这个周初鄂国的地望所在,学界曾有种种推测,随着湖北随州羊子山鄂国墓地的发现,学界普遍认为,周初鄂国即在今湖北随州安居镇一带。[75]传世“安州六器”之一的《中甗》铭文云:“王令中先省南国,……中省自方、邓,造□邦,在鄂师次。”现藏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静方鼎》铭文云:“王在成周太室,命静曰:‘俾汝司在曾、鄂师。’”两件青铜器年代在西周昭王时,可证昭王时鄂国仍在今湖北随州。[76]这是目前确切可考的鄂国地望。此外,西周厉王时期楚熊渠扩张,“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之“鄂”亦应在随州。[77]所以,我们也不能排除《楚居》鄂郢在随州的可能性。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则昭王时期的徙居地均在襄宜平原、随枣走廊一带,彼此相距并不甚远。这对我们理解《楚居》楚王的徙居地或许不无助益。
传世文献亦有楚昭王迁徙郢都的记载,《左传》定公六年:
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乎迁郢于鄀,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78]
《史记·楚世家》作:“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79]《吴越春秋》又有“徙于蒍若”事。[80]对于此次迁徙的不同称谓,学者有种种猜测。[81]但比较《楚居》的记载,应该就是指昭王从秦溪之上复徙袭美郢之事,鄀郢或蒍若应即《楚居》之美郢。至于为何一称美郢,一称鄀郢,尚待进一步研究。
四、结论
我们根据新发现的金文简牍材料,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重新检讨春秋晚期吴师入郢之役,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证实石泉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结论,即吴师一路西进,联合蔡国军队逾楚方城隘口南下,在今襄阳一带的汉水两岸与楚军决战,然后渡过汉水,长驱南进,攻入楚郢都。楚昭王君臣于郢都陷落前,“涉雎济江”,一路奔随,所经之地,都在今钟祥县境的汉水以东,路途并不遥远。而吴师所入之郢,及昭王逃离之都,就应该在湖北宜城平原上的蛮河下游,而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今江陵附近之沮漳河。出土文献所提供的最强有力之证据,在于《系年》有关晋吴联攻楚方城之记事。由此,传统说法的种种疑点,可以涣然冰释。
出土文献一方面证实了石泉先生学说体系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出土文献所反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即以楚郢都而言,在传世文献(以《左传》为代表)中,春秋时期除了“迁郢于鄀”外,鲜见楚王迁郢的记录,而出土文献《楚居》,仅昭王时期即有五次迁徙,涉及秦溪之上、美郢、鄂郢、为郢等四处地名,却并无迁鄀郢记录。另据《左传》和《史记》,昭王在击败吴师、收复失地之初,即曾“归入郢”,《左传》还明确记载吴人入郢后“争宫”事,则昭王所归之“郢”,应即吴师入郢前所居之“郢”,然则这一点却不见于《楚居》,或者说《楚居》中得不到证实。何以会如此?
石师曾坦承,他的研究方法,“主要依靠更早的先秦、两汉、六朝(直到齐梁时)的古注和经过认真鉴定的有关史料,以此与《左传》所记互相印证”,“跳出隋唐以来直至近世逐步形成的旧传统框框”,“进行了一番返本探源的重新考订”,从而得合乎历史本相的结论。换言之,先生只是怀疑隋唐以来所形成的解释体系,对先秦古籍尤其是《左传》是不怀疑的,或者说是基本信任的,这也无可厚非。这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使然。的确,假如否定《左传》的相关记载,我们还能用什么资料重构春秋时代那一段历史呢。
随着新发现的史料不断增多,在面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不同点时,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在二者互证互释的“二重证据法”之外,我们是否可以质疑早期文本的史料来源、探讨文本的编纂原则与形成过程、研究文本的传播及影响,这应该是今后的努力方向吧。
2017年12月3日初稿
2018年7月12日改定
注释:
[1]该文后以“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为题,正式发表于《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416页。上引文见该书“自序”,第10-12页。原文标题下附注(第355页):“本文初稿作于1944年春季,是在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时的毕业论文,由徐中舒教授教导。1955-1956年间,作过两次修改补充。1984年春夏间第四次修订稿中作了较多的增订和改写。这次定稿又作了一些订补。”该文后又收入《石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245页。引文见“自序”,第6-7页,文字略有增删,在上引文末另有一句“也是对流行的传统说法最早打开的重要突破口”。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與)、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本文所引金文简牍释文,凡不作讨论的字,皆从宽式书写,不作严格隶定。
[3]凡国栋:《曾侯与编钟铭文柬释》,《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4]高崇文:《曾侯与编钟铭文所记吴伐楚路线辨析——兼论春秋时期楚郢都地望》,《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引文见第83页。
[5]李零:《文峰塔M1出土钟铭补释》,《江汉考古》2015年第1期。
[6]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7-228页。
[7]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8]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67页。
[9]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80-183页。释文及标点据后续研究略有变动,与原释文略有不同。下文所引《系年》均同。相关后续研究在正文中随文列出,此不备举。
[10]李守奎:《清华简〈系年〉与吴师入郢新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24日第7版。
[11]李守奎:《清华简〈系年〉所记楚昭王时期吴晋联合伐楚解析》,罗运环主编《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90-97页;此据氏著《古文字与古史考——清华简整理与研究》,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22-134页,引文见第133页。
[12]参看陈民镇:《清华简〈系年〉研究》,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江林昌教授),2013年,第124-127页。
[13]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整理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999年版,第1540页。
[14]竹添进一郎(光鸿):《左氏会笺》,富山房,昭和五十三年(1978年)三版,定公四年,第18页。
[15]李学勤主编《春秋公羊传注疏》(整理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999年版,第555页。
[16]林丽霞、王凤剑:《南阳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铭铜器》,《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
[17]黄锦前:《“许子佗”与“许公佗”——兼谈清华简〈系年〉的可靠性》,简帛网2012年11月2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56)。
[18]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四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177-279页;收入氏著《石室剩言》,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6-214页;参看晏昌贵:《谈北大藏水陆里程简册中的几个地名》,韩宾娜主编《丙申舆地新论:2016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9]参看马孟龙:《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释地五则》,杨振红、邬文玲主编《简帛研究·2016秋冬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8页。
[20]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82页注释[一三]。
[21]陈伟:《读清华简〈系年〉札记》,《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
[22]黄锡全:《清华〈系年〉简所见“方城”“造于方城”等名称小议》,李守奎主编《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373页。
[23]参看程薇:《清华简〈系年〉与晋伐中山》,《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4]参看董珊:《读清华简〈系年〉》,收入氏著《简帛文献考释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107页。
[25]参看马楠:《清华简〈系年〉辑证》,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387页。
[26]参看(美)李惠仪:《〈左传〉的书写与解读》(文韬、许明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55页。
[27]李守奎:《清华简〈系年〉所记楚昭王时期吴晋联合伐楚解析》,收入《古文字与古史考》,第122-134页。
[28]马楠:《清华简〈系年〉辑证》,第384页。
[29]陈民镇:《清华简〈系年〉研究》,第124-127页。
[30]孙飞燕:《清华简〈系年〉初探》,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25页。
[31]孙飞燕:《清华简〈系年〉初探》,第150-153页。
[32]李学勤主编《春秋公羊传注疏》(整理点校本),第557页。
[3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春秋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图幅24-25。
[34]李学勤主编《春秋谷梁传注疏》(整理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999年版,第320页。“后事”,整理者据阮元校勘改作“一事”。
[35]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整理点校本),第1542页。
[36]杨树达《词诠》,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39页。
[37]尤锐(Yuri Pines):《从〈系年〉虚词的用法重审其文本的可靠性——兼初探〈系年〉原始资料的来源》,李守奎主编《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236-254页。
[3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与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释文参考了后续研究成果,参看韩宇娇:《曾国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赵平安教授),2014年,第146-158页;以及文中所引相关研究。
[39]整理者据李学勤意见,定在吴师入郢后九年,公元前497年,参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与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李学勤:《曾侯与编钟铭文前半释读》,《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徐少华据铜器风格和墓中出土器物,断其年代约在公元前480年左右的春秋末年,参徐少华:《论随州文峰塔一号墓的年代及其学术价值》,《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40]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247页;参看王宁:《上博九〈邦人不称〉释文补正简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网,2015年4月5日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482)。
[41]石泉师:《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401页;《石泉文集》,第239页。
[42]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81、190页。
[43]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88页。
[44]黄灵庚:《清华战国竹简〈楚居〉笺疏》,《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1期。
[45]赵平安:《〈楚居〉“为郢”考》,《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
[46]赵庆淼:《〈楚居〉“为郢”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年第3期。
[47]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89页。
[48]李守奎:《论清华简中的昭王居秦溪之上与昭王奔随》,《清华简研究》第1辑,中西书局,2012年;收入氏著《古文字与古史考——清华简整理与研究》,第116-121页。
[49]黄锡全《楚简秦溪、章华台略议——读清华简〈楚居〉札记之二》,简帛网2011年9月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41),后收入罗运环主编《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89-196页。
[50]赵平安:《〈楚居〉“秦溪”考》,载《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李学勤先生八十寿诞纪念文集》,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324-327页。
[51]参看肖洋:《吴人入郢后楚昭王不可能迁居〈左传〉所言之“乾溪”》,罗运环主编《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44-248页。
[52]徐少华:《论随州文峰塔一号墓的年代及其学术价值》,《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53]陈伟:《曾侯与编钟“汭土”试说》,《江汉考古》2015年第1期。
[54]李学勤:《曾侯与编钟铭文前半释读》,《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正月曾侯与编钟铭文前半详解》,《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4期。
[55]韩宇娇:《曾国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赵平安教授),2014年,第248页。
[56]王恩田:《曾侯与编钟释读订补》,《出土文献研究》第15辑,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48-55页。
[57]参看晏昌贵:《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新探》,《考古学报》2016年第3期。
[58]《周礼·夏官·职方氏》讲九州山川,其中豫州“其川荧贿。其浸波溠”,可见溠水闻名当时。但溠水在随枣走廊却属豫州,颇为费解。
[59]《春秋左传正义》(整理点校本),第1561页。
[60]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70页。
[6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73页。

[62]袁金平、张慧颖:《清华简〈系年〉“析”地辨正》,《简帛研究201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6页。
[63]李守奎:《论清华简中的昭王居秦溪之上与昭王奔随》,收入氏著《古文字与古史考——清华简整理与研究》,第120页。
[64]《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398页。
[65]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186页;参看黄人二:《上博藏简〈昭王毁室〉试释》,《考古学报》2008年第4期;黄国辉:《重论上博简〈昭王毁室〉的文本与思想》,《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
[66]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第187-190页。
[67]《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3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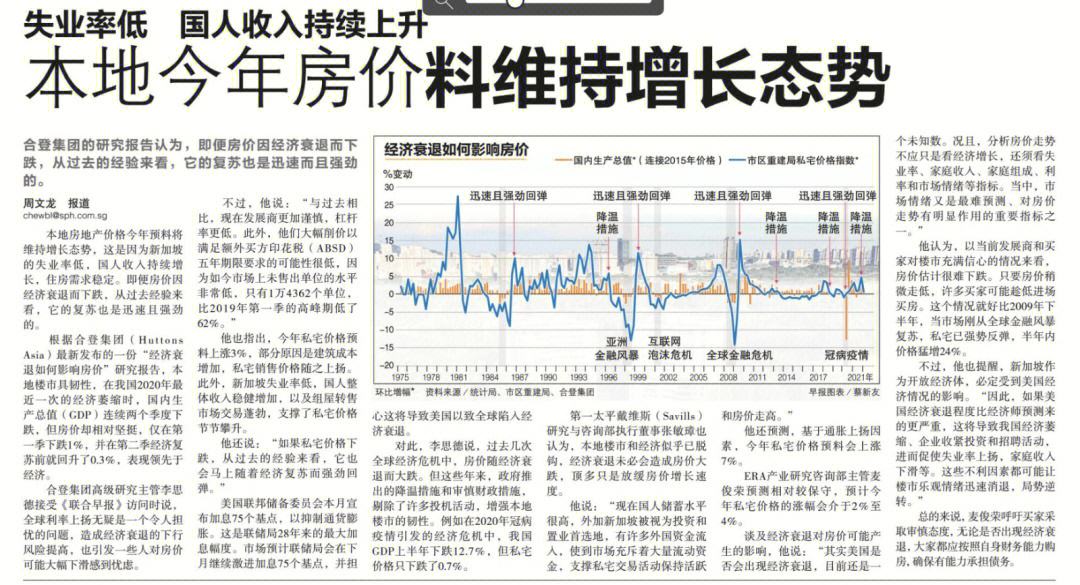
[68]牛鹏涛:《清华简〈楚居〉“媺郢”“鄂郢”考》,载《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李学勤先生八十寿诞纪念文集》,第351-354页。
[69]《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184、388-389页。
[70]《左氏会笺》,定公五年,第44页。
[7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第190页。
[72]黄灵庚:《清华战国竹简〈楚居〉笺疏》,《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1期。
[73]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6期。
[74]参看李学勤:《论周初的鄂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
[75]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文物》2011年第11期。
[76]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
[77]参看晏昌贵、郭涛:《<鄂君启节>铭文地理研究二题》,《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5期;另参高崇文:《从曾、鄂考古发现谈周昭王伐楚路线》,《江汉考古》2017年第4期。
[78]《春秋左传正义》(整理点校本),第1566页。
[79]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6页。
[80]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第67页。
[81]牛鹏涛:《清华简〈楚居〉与“迁郢于鄀”考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赵平安:《〈吴越春秋〉“徙于蒍若”考辨》,罗运环主编《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9-80页。
本文原载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石泉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23年1月,第40-55页。







